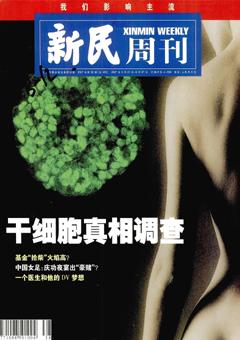基因的河流
邊 芹

諾曼人現(xiàn)在在地圖上是找不到了,這是征服者的命運,但你不知道這顆星球有多少人身上流著他們的血液,那條基因的河流邊界在哪里?
頂著時間為我預置的沉默,我已經(jīng)不以年作希望的代碼,我的思緒是百年一個臺階,千年一個檻?我也說不清在第幾個臺階上,總之文明城堡被攻克時,從來是無聲無息的,大眾在慶功的歌舞升平中陶醉,他們在血泊中也同樣會陶醉,他們看不見早已暗中設計好的棋路,也意識不到被偷換掉的棋子,他們只有他們的本能:站在勝利者一邊?
我最近連看了幾部歐洲考古紀錄片,多半是偶然挖到個遠古墓穴,一般都在紀年前一千年,甚至更早?以為消失了甚至根本不知其存在的文明,卻深埋在某處,我對這樣的謎百嚼不厭?看多了便發(fā)現(xiàn)文明的裂口——新涂油漆下面的裂口:掘出墓穴的地區(qū)現(xiàn)今生活著的人群,與墓葬里的精制文明掛不上鉤?你只要把眼睛從地下向上挪,便看到了驚人的裂縫:這些渾渾噩噩的人群,數(shù)千年前創(chuàng)造過那樣的文明?事物與軌道有時會出人意料地錯開,埋藏在地下的文明越輝煌,發(fā)掘的地區(qū)越落后,有些從文字到歷史都與現(xiàn)今處在它數(shù)米之上的人脫了干系?真讓人愁腸百轉!
8月末,追著即將鉆入秋景的暑氣,跑到巴黎西郊圣·日爾曼·昂萊城堡,轉了一圈考古博物館?那地方游客是不去的,時常是我一人穿行在石?骨?銅?鐵?金這些遠古的遺存物間,有徹骨冰涼的醒悟,仿佛一身的血肉被卸掉,只隔著一副骨架,去拂拭構筑時間的那些無用物品?高盧這塊地方,別看現(xiàn)在擺出這么副天下無物的架勢,地下可沒挖出什么寶?記得我從前在國內(nèi)往西北跑,直遛到馬步芳的舊宅才找著西寧博物館,里面人影晃不出半個,燈都懶得開,我探進身子,一個鄉(xiāng)下婦人從暗處站起來,邁著蒙古種特有的提不起的步子專為我開了燈?法國這家考古博物館,若只算地下挖出的東西,也就差不多西寧的水平?盧浮宮?吉美博物館的豐厚,都是從別人的地下搜羅來的?有很多地方是地下比地上富貴,這里正相反?千萬年后,地上的翻到地下,那才是文明的一頁,兩百年論成敗,還是心急和自負了一點?
我最后看的那部紀錄片,講保加利亞發(fā)掘的一個墓葬,距今也有三千多年,只是挖出的東西手工之精,尤其是金器,直讓你扣心自問:人在三千年的淘洗中究竟光亮了多少?時間是無法為金器點上句號的,那專制的手隨意涂抹其他材質,到了它面前就難下手?所以我看著挖掘者輕輕把它們身上三千年的塵土彈去,時間未能添加任何多余的裝飾,那面具隔著千年隧道也沒有收斂嘲笑世界的目光?你再看生活在地上的人,以及圍繞著他們的物品,才意識到文明不知何時已被切斷,切斷的時候細語輕聲,并非改朝換代那般突兀,時間跨度可能數(shù)百年之久,一點點褪去顏色,不知不覺就換了模樣?野蠻人螞蟻一樣攻占了城堡,血液被稀釋,城堡坍塌時,文明已經(jīng)大半個身子入土,但攻占者繼續(xù)在廢墟上繁衍,然后又有新的劫掠者參與其中?基因的河流沒有別的秘訣,就是糾纏?混雜,流向所有可以流經(jīng)的地方?
這是所有清醒而精制的文明之結局——被偷梁換柱?這個世界有財富的戰(zhàn)爭,還有暗中進行的基因的戰(zhàn)爭?說文明越走越燦爛是癡人說夢,只是它的墮落沒有幾人看得見,那自由落體的感覺幾乎讓所有人迷醉,這讓我時常有被時間巖石預先埋葬的感覺?基因的游走,在哪里被截住,又流向哪里?你以為確定的事,并不確定?法國有一個著名考古學家,他說自己一直自認地道布列塔尼人,因為母親是那里人,但某天他的美國同行從他嘴里搜集了一點口水,拿去實驗室,不久便告訴他,他的遠祖來自亞洲?我那天聽了這話,細看他的面相,每一根線條都好像遠古先人走過的地方?布列塔尼這塊伸向大西洋的尖地,分布著諾曼人的后代?讀愛默森《英國人的靈魂》時,看過對諾曼人的描述,這是個強盜民族,查理大帝有一次望著打劫完的諾曼人駕船離港,直掉眼淚,因為他想到他的后人遭遇這樣的民族,是要倒霉的?這個征服者民族是今天統(tǒng)治世界的盎格魯-撒克遜人遠古先人的構成之一?后來的確大半個地球都遭了殃,可見查理大帝的眼淚之英明?諾曼人現(xiàn)在在地圖上是找不到了,這是征服者的命運,但你不知道這顆星球有多少人身上流著他們的血液,那條基因的河流邊界在哪里?看不到那暗流,你沒法確定你從哪里來,你也不知道那些埋藏在地下的文明游走到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