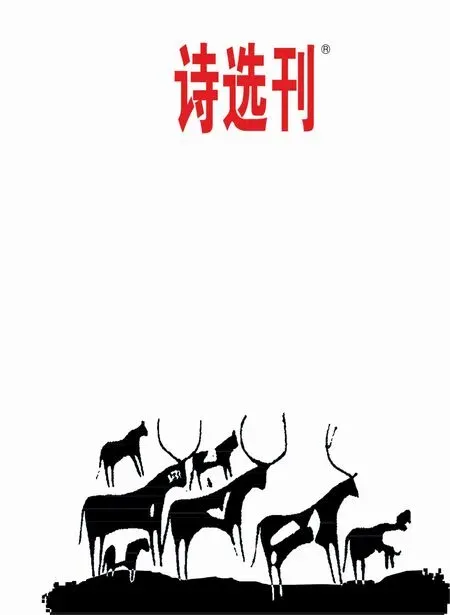當(dāng)故里漸漸地變成一個(gè)虛詞
帕 男
當(dāng)故里漸漸地變成一個(gè)虛詞
帕 男
在 他 鄉(xiāng)
記憶中 有很多燕子
在故鄉(xiāng)的屋檐下 那時(shí)我也在故鄉(xiāng)的屋檐下
埋頭生長
燕子總是謙遜地
和我呢喃 我懷疑 那些燕子
總是錯(cuò)把他鄉(xiāng) 當(dāng)故鄉(xiāng)
盡管我多年不回家了 可母親還在故鄉(xiāng)屋檐下
佝僂著身子 接受著 時(shí)間的賞罰
母親也叨絮過
說我也變成了那些燕子
如果 我真是一只燕子 倒也心安理得
在別人的屋檐下
怕則怕
春后 那些燕子
將春天的瘡疤摳開
這樣的處罰
還不如 在他鄉(xiāng)的屋檐下
允許我殘存一丁點(diǎn)記憶
不管朝夕 都向著春的那邊呢喃
裝在畫框里的故鄉(xiāng)
就在節(jié)骨眼上 撒一坡草
營造故鄉(xiāng)的氛圍 然后對(duì)我的子孫說
那時(shí)候 牛在畫框里
等著我們
畫一個(gè)蓑笠翁 但不畫雪
也不畫扁舟
更不畫魚
只畫我 再畫一對(duì)酒杯
月會(huì)從畫框里下來
再點(diǎn)綴些狗吠 籬笆疏影
我不敢說 這就是故鄉(xiāng)
倒更像敗筆
擬聲太難了 不是金屬碰著金屬
也不是肉體碰著肉體
是念想碰著念想
葬 鳥 記
一大早 我素葬了一只鳥
準(zhǔn)確地講 素葬的一只麻雀
我喊一個(gè)我曾經(jīng)熟悉的鳥的名字
但沒有應(yīng)答
證明我熟悉的那只鳥
并不認(rèn)識(shí)我
素葬這只鳥 我沒有厚此薄彼的意思
我爺爺死了是素葬
奶奶也是
父親也是
素葬這只鳥 等于同等相待
想問的是誰阻斷了這只鳥的夢(mèng)想
都知道 麻雀是不走夜路的
又怎么可能死在了天亮之前
鳥是死了 即便是我不熟悉的
我都不能不管 這只鳥死在了我的地盤上
高高曇華山
你來不來 這座山也不會(huì)寂寞
老畢摩的那一陣清咳
我懂 每到午后
他都會(huì)
和這座山的
某一棵樹
搭白 我懂 即便是一顆羊肝石
也會(huì)哼幾句
放羊調(diào)
村 落
我已不大注意村落 以那些人的脈象
看不出 村里人
有要拋家離舍的征兆
只是犁耙和鋤頭
遠(yuǎn)離了
稼穡 像文言文里的介詞
這些介詞
不由分說地
占據(jù)了出村的所有道口
我不得不 將方言
一字一句地
譯成普通話
好讓城里人也能讀懂
當(dāng)那些稼穡的工具 也漸漸地
變成 我的遠(yuǎn)房親戚
即便偶爾遇著了 最多
我也只是點(diǎn)點(diǎn)頭 就算彼此打個(gè)招呼
也不會(huì)問 多年漂泊
之后 還有幾人注意村里人的脈象
做個(gè)東晉男人
做個(gè)東晉男人
首先不能談九月 九月叫菊的女子太多
但我從來就沒有認(rèn)識(shí)過一個(gè)叫菊的
據(jù)說男人都好菊 菊在東籬下
東晉姓陶那個(gè)酒鬼
肯定是醒也菊來醉也菊的
如此癲癡
為菊
姓陶的一句“此中有真意”
這一讀就讓我讀了一千五百年
到現(xiàn)在還似懂非懂
做個(gè)東晉男人
其次必須要有公斤級(jí)的酒量
東晉那幾個(gè)大酒鬼 哪個(gè)不是
少則三五斗 多則一兩斛
和豬同飲 醉了裸奔
和劉伶比 我只能算個(gè)酒孫子
但我與酒肝膽相照
我從不信別人說什么“酒里乾坤大”
也就從不信別人說什么“壺中日月長”
當(dāng)故里漸漸地變成一個(gè)虛詞
給我一個(gè)地名 然后讓我指認(rèn)
這就是故里
像被雪藏過 這樣的故里
顯然僵硬
多一個(gè)故里
就又多了一次贖罪
尤其 當(dāng)故里漸漸地變成一個(gè)虛詞
我必定被拒之于文本之外
別無他物 別無他物